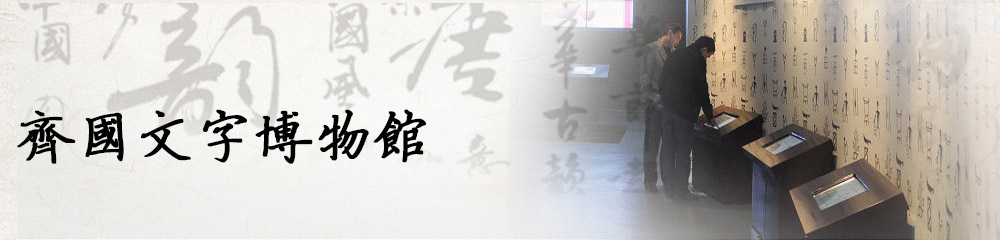临淄齐国封泥群史料探绎
孙慰祖
临淄封泥发现之历史回顾
山东临淄是早期出土古代封泥的地区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陈介祺获得“姑幕丞印”封泥,致书吴云曰,“东土竟亦有封泥”(《簠斋尺牍》)。从他的语气中可以看出,自道光年间就开始收藏封泥的陈氏,至此时方获知本地发现封泥的消息。此泥后来辑入《封泥考略》。陈氏所藏封泥中,还有若干可勘定为临淄所出。
同时收集临淄封泥的还有郭裕之。罗振玉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郑庵所藏封泥》一书,所收一百四十八枚即为郭氏藏品。除四件疑伪、少数未能确定出土地外,约有百余枚可信为临淄所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郭藏封泥文字风格、泥型以及官名、地名所涉范围,都和后来临淄刘家寨陆续发现的封泥属于同一系统。1913年,罗振玉辑成的《齐鲁封泥集存》是最早按出土地域编集的封泥专谱,此书将郭氏收藏与刘鹗《铁云藏封泥》辑入的临淄封泥汇合为一,又加入了罗氏自藏的六十四枚封泥。接踵收集临淄封泥者除郭裕之外,还有高鸿裁、王懿荣、丁树桢、孙文澜、周进、陈宝琛等人。但此期所出的具体地点,未见记载。
据笔者校勘,陈宝琛所收临淄封泥约百余枚,合以关中、蜀地所出者于1924年拓成《澄秋馆藏古封泥》。丁树桢所获封泥,后转归周进。周进从弟周明泰于1928年辑成《续封泥考略》六卷。周氏封泥共四百五十余枚,绝大多数为临淄所出。
郭裕之所藏一百七十余枚,后归国立北京大学。1934年,北大研究部据此编成《封泥存真》一卷,其中大半已见于罗氏《齐鲁封泥集存》。
今临淄齐都镇北郊的刘家寨,位于齐故城内大城之中区。1936年王献唐撰《临淄封泥文字叙》,对其地出土封泥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载。王氏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临淄县城北刘家寨附近农田出土封泥一坑,共得一百余枚。次年,县城东门外偏北一带农人制砖时又掘获一坑。刘家寨一带先后发掘封泥遗存达十余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刘家寨村农田中又发现数十枚封泥,而后村民挖掘不止。
王献唐又记述,县城东门外所出多见秦封泥,印文有栏格;刘家寨所出则无界栏。则东门外存在秦代官署遗址。
1934年,王献唐为山东省立图书馆征集得五百余枚(其中包括孙文澜所获的八十余枚)。两年后,编辑成《临淄封泥文字》十卷。这部分封泥后来转归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由此看来,齐故城内是山东地区秦汉封泥最集中的发现地。
1958年,临淄考古队曾在刘家寨作过短期的小规模调查试掘,于刘家寨村西侧T102探沟中出土封泥四十余枚(《考古》1961年六期刊《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 。这一发掘所获与三十年代前后刘家寨出土封泥的时代属性相一致,职官内容也有相当部分的重合,仍属于西汉初齐国及其属县、乡的封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又对刘家寨做了一次勘测,已经探明此处周围有多处夯土建筑遗址及冶铁遗址。根据对该地历史上所出封泥职官类别及时代的分析,可进一步作出判断:封泥发现地应为西汉齐国王宫、行政机构、库府、作坊等所在,包括除国后齐郡府署遗址在内。
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公私各家比较集中收藏的临淄出土封泥约为一千三百枚。
2003年秋,笔者因馆务赴临朐、青州,折道往临淄,冀以考察早年出土封泥地点之概貌,阻于齐故城一带正大规模拓路而未果。承时任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玉德先生告知,近年附近村民偶有携封泥来馆,但索价较高,大多难以征集。2005年8月,笔者赴潍坊参加“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其间在临淄政协武守南先生协助下踏访了刘家寨新出封泥的地点。该地以西的公路边,现仍残存一段古城墙,村口有一“刘家寨”石牌。据陪同的文管所同志指引,出土封泥的位置在村落南部的一片玉米地中,当时被人挖掘的面积约二十平方米。而据考古勘测确定,周围存在古代居住遗址及夯土建筑。这与封泥出土具有内在联系,也证实了此前一部分流散封泥的来源可能即出自这一区域。
2006年第九期《考古》刊出《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内出土汉代封泥》一文,报道了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征集得故城南部发现的四十二枚封泥。这一消息,进一步确认了出土封泥的区域。
近年陆续见于发表、传出于临淄的封泥,数量超出四十年代前所出的总和,品类大多与早年出土的重合,主要属汉初刘氏齐国及其属郡辖县、乡官印一系。也有一小部分据文字可知时代上限为战国,下限为西汉中晚期与东汉前期。这似可提示,近年齐故城一带又有多个出土地点的发现。
2018年8月,笔者受中国印学博物馆之邀,与筹展同志前往临淄鉴选展品。经向当地知情人士了解,近年刘家寨及周边确有多处出土封泥。在刘家寨村南、东关村北的路边及刘家寨村察看,传曾为当地村民捡获封泥的几个地点,地表均可见陶器、陶瓦碎片。很明显,附近应为古代建筑遗址所在。
据齐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告知,近年在刘家寨西北的葛家庄流出的官印封泥,印文地名含有去齐地较远的汉郡县。从文字风格和泥型上看,时代多晚于此前刘家寨所出刘齐王国一系的封泥,则表明该地存在另一个时期的官署遗址。但以目前已有资料来看,临淄所出封泥主体仍为西汉早期刘齐王国及支郡所辖的县、邑、乡官印文字,可以视为同一体系。也由于这一特征,本文以齐国封泥群所保存的官制、地理史料为探析的重点,首先对《汉书·诸侯王表第二》序所载汉初诸侯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体制和刘齐王国—齐郡—东汉齐国时期的行政联系范围作一梳理。
临淄封泥所见西汉齐国官制与地理
临淄新出土封泥多已流散,难以确切统计数量。由《齐鲁封泥集存》《封泥存真》《续封泥考略》《临淄封泥文字》《新出封泥汇编》诸书所辑,以及此次展出的封泥为主要资料范围,可提取出这一封泥群所含职官的主要类别:
一、王国诸卿及其属官;
二、王国支郡及辖县、邑、乡官;
三、王国封域以外之郡、县、邑、乡官。
朝官系统下行之官印,在以往临淄封泥中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览首次公布的“服官令印”(L005)“服官右尉”(L008)“服官金丞”(L009)“技巧火丞”(L010)“武库丞印”(L011)等封泥具有重要的价值。新发现的“齐服官丞”(L081)“齐服官监”(L080),应与中央所置职官构成对应关系,故文献失载的朝官体系中置有“服官”一职由此获得了补正。《汉书·地理志》载齐临淄有“服官、铁官”,考古工作者在此前勘查中已明确刘家寨及附近的冶铁遗址与居住地区遗址。现在多枚“服官金丞”“金丞”“齐服官丞”“齐织官长”(L083)封泥的发现,以及过去刘家寨曾出土“齐铁官印”(L077)“齐铁官长”“齐铁官丞”和“齐武库丞”等封泥,这些实物资料不仅证明了其地有服官、织官、铁官与武库之官署的存在,也揭示了汉代对主要产业如采金业、冶铁业、盐业等,实行中央与郡国双重管理的体制。
临淄封泥中,属于前揭一类、二类职官印文的数量最多,且往往重见。根据这样的构成情况,封泥群反映出当时行政联系以齐国内部最为频密,属于刘齐支郡以及文帝十六年后削出另立之王国者亦有若干,如“齐昌守丞”“临淄丞相”“淄川王玺”“淄川中尉”“淄川内史”等。
关于王国官制,《史记》《汉书》并无系统集中的记载。今益以近年新出者,可以征得齐国诸卿及属官职名达八十一种(不包括郡、县官属),其所置诸卿和属官与中央王朝的体系基本对应,而且出现了不少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未载的官属,因而得以由王国反证《百官表》所阙略之朝廷职官记载。这是目前有关汉代诸侯王国官制最为集中的一批史料,比之传世文献记载和其他出土实物资料,尤具有详实性、确定性和系统性。
临淄封泥所反映的刘齐王国诸卿官制,可以说是“七国之乱”前整个西汉诸侯王国官制的缩影,从职官体系方面有力地证明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势益大,与天子“尊无异等”的状况。
临淄封泥所见齐国诸卿及属官可归纳为下表:
《新出封泥汇编》辑录有以下齐地封泥为前所未见,亦属王国官属:
齐文园长、齐文寝长、齐祝长印、祠官之印,为太常属官。
齐御史丞,为御史大夫佐官。
齐乐府长、齐宫司长、少府市印,为少府属官。
齐家马丞,太仆属官。
齐家丞印,王国“家丞”,当为太子宫之属官。
齐正之印,未明职事。待考。
此次展出的“齐服官丞”“齐织官长”“齐服缕丞”又得以补充齐官三种。
目前所获封泥揭出的职官名,虽不能尽涵当时齐国置官之所有,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基本还原了史籍缺略的汉王国官制体系。汉初王国置官之周备细密由此可以一目了然。这是临淄封泥中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
临淄封泥中含有数量众多之县、邑、乡官印文字,其中所涉行政地名,应为两个部分。
一为汉初王国所领支郡辖县。《汉书·高帝纪》,高帝六年,“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据周振鹤考,刘肥之齐国,尚领有琅邪一郡,计得七郡之数。(《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今存西汉早期封泥中,有“济北守印”“临淄守印”“城阳郡尉”,皆刘肥所领支郡之官。这些封泥确定为齐国之属的依据是,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则上述封泥必在此前;又,文帝十六年以临淄郡分置齐、淄川两王国,济北在文帝十六年封为刘肥之子刘志王国,则皆不得再有“郡守”;城阳亦在同年封刘喜,则其为刘齐支郡而有“郡尉”的时间必在此前。此次展出新获封泥“齐郡守丞”(L012),则系武帝除齐国为齐郡后所置,故文字风格与前数者亦有区别,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史籍所载。
齐国初封之时,地域广远,辖县颇多。于历年所出封泥中获见的县、邑之数达六十八个:
茬平、东阿、寿良、定陵、女阴、博阳、宛、邓、阜陵、建阳、郜、元城、元氏、平棘、东光、高唐、博昌、狄、琅槐、乐安、高宛、东平陵、台、粱邹、于陵、般阳、菅、蓍、奉高、卢、来无、临淄、昌国、利、西安、广、临朐、营陵、益、平寿、都昌、平城、夜、黄、昌阳、茀其、朱虚、姑幕、梃、计斤、东海、即丘、淮浦、南昌、辟阳、南宫、勮、东安平、即墨、下密、郁秩、高密、筥、磨、海、郊、委壤、卫。
以上县、邑,以分布于汉初胶东郡、胶西郡、临淄郡、济北郡最为密集,其所涉范围主要在西起博平,东至东牟,北及乐陵,南抵下邳这样一个区间,仅部分县邑越出此域。这与文献中求得的高祖六年齐国所领七郡的地域大致相当,封泥文字风格与其所反映的齐国封域之变迁也可形成互证。即大部分县、邑应属于文帝十六年前之全齐的时期。其后琅邪属汉,余六郡分置七国,齐王将闾所领仅临淄郡之一部,与削出之郡县不至于存在如此广泛、频密之联系。
近年来新见的封泥资料,如果所传出土地点得到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实,则对于认识西汉齐国封域内外之行政联系状况及两汉地理沿革,都具有参考意义。
另有一部分封泥来自全齐时期封域之外者,如彭城、宁陵、平都、卢奴、荧阳、长安、新丰等县。此次展出封泥县邑范围又有所扩大,所见地名来自淄川、胶东、济南、泰山、东莱、楚、北海、千乘、江夏、东海、城阳、常山、东郡、涿郡、豫章、庐江、九江、信都等郡国,对于了解汉代临淄所在官署与其他地区行政联系的范围,显然是值得重视的材料。
如果我们深入辨析此次展览部分封泥的时代风格及泥型,如“新息长印”(L108)“平棘邑丞”(L115)“合肥丞印”(L110)“东海盐丞”(L017)“居巢尉印”(L112)“淮浦左尉”(L060)“南昌丞印”(L046)等,分别属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遗物,经向齐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了解,这部分封泥传为葛家庄某处发现,则刘家寨周边存在景帝削齐以及武帝除国为齐郡后的官署遗址,时代延续至东汉。故这批封泥的发现,与齐国文字博物馆所藏新出战国齐系封泥“戠内帀鉨”(L001)“吉杢遂鉨”(L002)“乔㥩信鉨”(L003),刷新了我们对临淄出土封泥时代序列的认识。
在齐地县邑之中,以临淄县之封泥品类最多。盖两汉临淄均为王都或郡治所在,其置官最为齐备亦在情理之中,除通常的县令、长、丞、尉外,尚见有若干特设之官。如过去出土者“临淄市丞”“临淄铁丞”“临淄卒尉”。《新出封泥汇编》辑入临淄所出“左库之印”“库印”“右市”“西市”“市府”封泥,也是郡、县所设各种机构,其出土地与府库、市易事务存在一定关系,惜与临淄大多数封泥的情况一样,出土的具体地点已经无由证实。
近十多年中,新见封泥尚有若干其地无考、侯名失载之侯邑,如海邑、卫邑、委壤侯国。其中卫、委壤为以往未有之地名,证实汉初齐地或相邻区域当有此侯邑。而可考得其封年与侯名的封泥有:请郭邑丞(《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作清都侯)、广侯邑丞、博阳邑丞、利邑丞印、都昌侯相、郊侯邑丞、辟阳邑丞、平都邑丞、营侯丞印、阜陵邑丞、强侯邑丞。另有其地可考而侯名未载于汉表之例,如:益邑丞印、定陵邑丞,《汉书·地理志》载益、定陵分别属北海、颖川郡。今封泥文字见其地置其“邑丞”,可证西汉曾为侯邑。
以上侯国、邑多为高帝所封之功臣侯,其除年也基本上在景帝初年以前。这是新出临淄封泥断代的又一重要参照。
历来临淄所出的封泥中,值得重视的另一部分地名资料是大量乡官印文。这是其他封泥群未有的规模。笔者统计有如下之乡名:
安乡、安国乡、安平乡、白水乡、北乡、昌门乡、昌乡、成乡、朝阳乡、定乡、东闾乡、东乡、都乡、端乡、高望乡、高乡、句莫乡、广陵乡、广文乡、广乡、画乡、建乡、勮里乡、軦乡、利居乡、利乡、路乡、吕乡、良乡、南乡、南成乡、平望乡、祁乡、请乡、上东阳乡、尚父乡、台乡、宛乡、武乡、西昌乡、西平乡、西乡、新息乡、信安乡、休乡、阳夏乡、宜春乡、益利乡、郁狼乡、犹乡、右乡、原乡、渍郭乡、昭乡、正乡、中乡、左乡。
这些乡官印文多含有鲜明的秦篆因素,表明其时代多属汉初,也应是考虑临淄封泥性质的一个因素。汉初每县所辖之乡,约不超出四乡。这些乡印的来源当不止于临淄郡一地,它与前文所举县、邑的地理范围,当可相互呼应,皆揭示出土上述封泥的遗址既非临淄县,亦非临淄郡的官署。
汉代的地理文献,所记载的范围基本上止于县、道、国、邑,故对于乡与县的沿革关系,没有多少线索可寻。秦汉时的县是由邑、聚发展演化而来的,这是建立郡县制的基础之一。《史记·秦本纪》说,“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汉代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之中。按《地理志》所记,西汉末的县数已较秦时扩增五百余。其中一部分升格为县后仍沿用了原来的乡名,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一些属单音节名词的县,后来仍遗有“乡”字,如“台乡”“祁乡”“广乡”“西乡”“武乡”“定乡”等县。如果提取历来临淄封泥中的乡名,与《史记》《汉书》表志中所见的县、侯国相考校,同名者多见。这类地名至今在各地尚见保留,虽不能确定同名乡、县必为对应,亦不能均视为偶然重名。这些封泥文字为探讨乡—县的沿革关系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结合这些乡印封泥的文字特征来考虑,这些乡的建置,主要是秦、汉之际推行其郡、县、邑、乡行政体制过程中形成的。我认为一部分乡印或可入秦,而在汉初仍然袭用。
临淄封泥的形态与文字特征
由上所论,目前新见临淄封泥的出土地点,较历史上的发现已有增多,时代跨度也因此而进一步延展,此次展出的封泥在形态与文字风格上,都体现了临淄封泥的这一特点。
从拓片复印件可推知,各个时期所出封泥,形态大多为A型(关于封泥分型,见拙撰《封泥的断代与辨伪》,刊《可斋论印新稿》,2003年3月)。泥背之检痕有宽、窄两种。近十多年来新见封泥印文风格大多与过去出土的基本相同,故其封检方式与形态亦必为同一类型。A型封泥的流行时间在秦至西汉早期,结合刘齐王国封域沿革来看,此类封泥下限亦不晚至景帝。
刘家寨所出西汉早期封泥文字与同期汉朝官印、其他郡国官印文字相比较,地域的风格也很明显。齐国官印封泥大多较小,印文风格总体上不如朝官印平整规矩,一部分文字还有草率的倾向,如“临淄右尉”“齐铁官长”“临朐丞印”“齐都水长”等。在乡官印中,其表现尤为明显。究其原因乃是汉初诸侯王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并且自铸自颁官印所导致的现象。但在历史上发现的临淄封泥中,也已经有少量西汉中晚期遗物的出土,如“临淄卒尉”一类。此次展出的一部分形态为B型、C型,文字风格为西汉中期以后的朝官、郡县官印封泥,和刘齐王国诸卿系统及支郡辖县官印封泥又有不同,表明出土地点或已越出此前的范围。这部分印文形态更为方正,泥色也有异于齐地封泥。
临淄封泥中也存在不少同文官印,细加分析却非同模所出,此种现象在陕西、河南所出秦、西汉、东汉封泥中均见存在。这是透析秦汉时代官印制作状况的颇有说服力的信证。如王国诸卿属官“齐内史印”“齐内官丞”“齐宫司丞”等等都出有多种,所呈现的同文异范特征,足以说明同一职官印章存在多次更铸的现象,这使我们重新认识职官印与官署印两种不同制度下,官印制作、颁缴的差别,而中国真正实行以官署印为主的制度,是在隋唐时期。
在消歇了五十多年后,刘家寨及毗邻地区再度比较集中地出现以齐国遗存为主的封泥,数量既多,而又含有不少此前未有的职官、地理史料,带来了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这批封泥资料虽因非科学发掘导致了某些信息的丢失,但经与以往所出封泥的比较,其中王国与县、乡官印体系,相当完整地得到保存,其边界亦比较明确;而过去未曾出现的一部分非齐国系统的封泥——即来自朝官及其他郡国的官印封泥,当可与早期的发现形成互补,这对于研讨西汉王国官制、齐国封域沿革和两汉时期临淄与各地的联系,都提供了史籍所不具备的独特条件,也为认识临淄齐故城多处遗址的性质带来了新的线索。
就目前发现的若干封泥群而言,西汉齐国遗存为主体的临淄封泥群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学术内涵。山东九宫阁齐国文字博物馆多年来悉心藏护齐地所出封泥,于齐文化之传承研究颇有建树,此次由该馆提供新获品类,与中国印学博物馆共同策划此次学术展事,并刊行图录以广播扬,将成为古代封泥研究史上一个新的纪录。从此次展览的特点来看,以上自战国、下至东汉这样一个时代跨度内的地域封泥群构成体系,在提供艺术观赏、探讨而外,更凸现出引领人们去发现展品所涵多方位研究课题的策展理念,其学术立意是极具创见的。